- 全部分类/
- 生活艺术/
- 视野
 扫码免费借阅
扫码免费借阅
目录
快速导航-

导读 | 导读
导读 | 导读
-

视点 | AI会演变成一种新人类吗?
视点 | AI会演变成一种新人类吗?
-

视点 | AI能理解人类的情感吗?
视点 | AI能理解人类的情感吗?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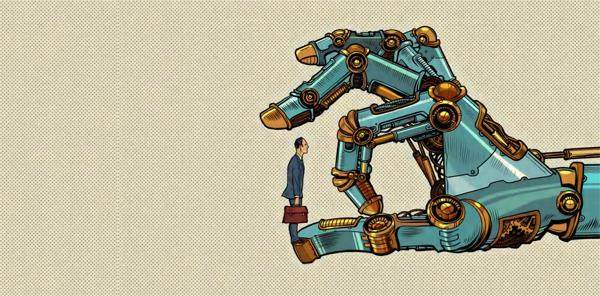
视点 | AI可以建立自我意识吗?
视点 | AI可以建立自我意识吗?
-

视点 | 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吗?
视点 | 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吗?
-

视点 | AI写文章又快又好,学语文还有用吗?
视点 | AI写文章又快又好,学语文还有用吗?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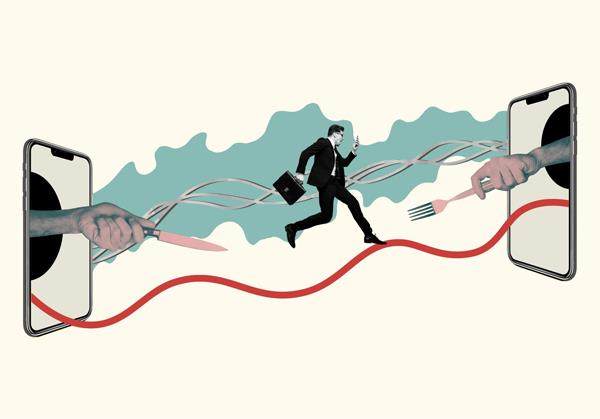
视点 | AI面前,保持清醒
视点 | AI面前,保持清醒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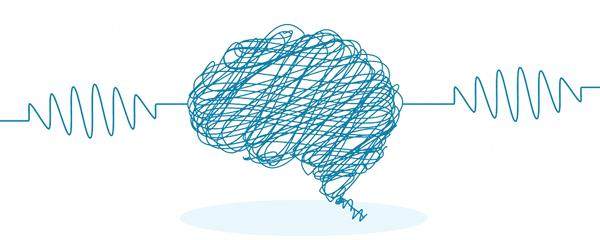
大学之大 | 千万别擦科学家的黑板
大学之大 | 千万别擦科学家的黑板
-

大学之大 | 高职毕业,我在清华当老师
大学之大 | 高职毕业,我在清华当老师
-

大学之大 | 当AI入侵大学论文
大学之大 | 当AI入侵大学论文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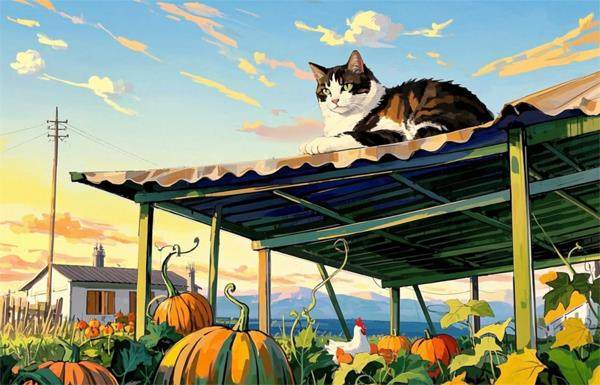
美育 | 天棚里的猫
美育 | 天棚里的猫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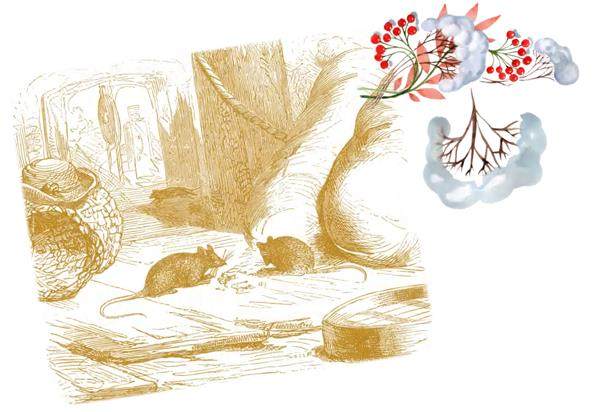
美育 | 等一只老鼠老死
美育 | 等一只老鼠老死
-

美育 | 孤鸿杜丽娘
美育 | 孤鸿杜丽娘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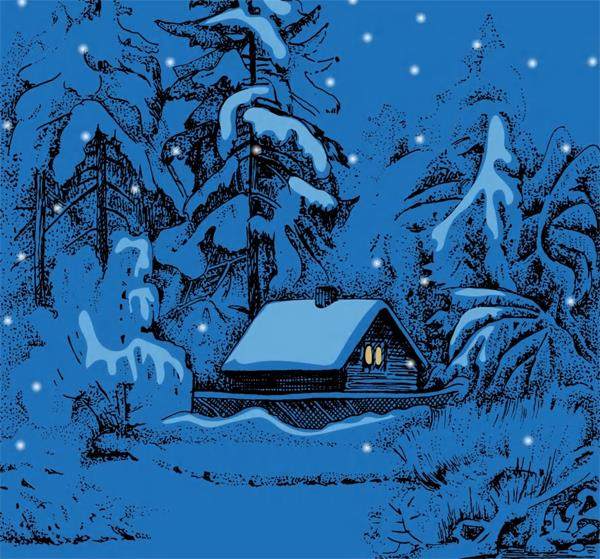
美育 | 雪四章
美育 | 雪四章
-

美育 | 唐落霞式“彩凤鸣岐”七弦琴
美育 | 唐落霞式“彩凤鸣岐”七弦琴
-

美育 |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异形器
美育 |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异形器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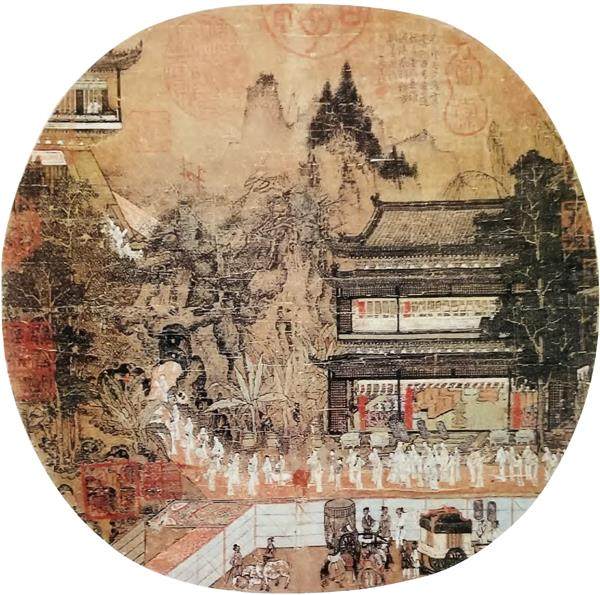
美育 | 中国绘画欣赏
美育 | 中国绘画欣赏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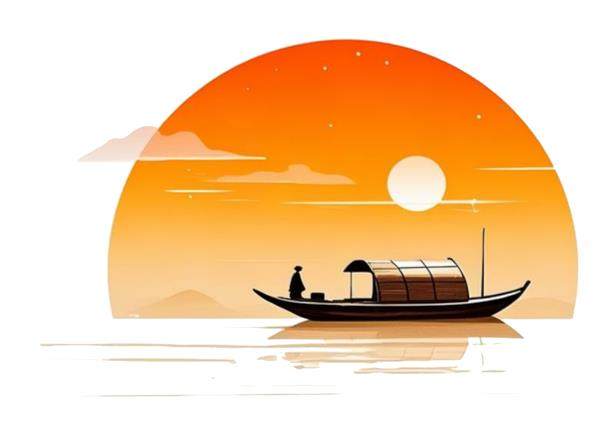
美育 | 看落日顺便复习了一首白居易
美育 | 看落日顺便复习了一首白居易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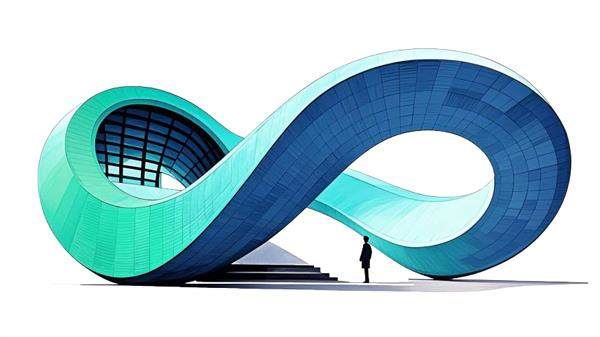
美育 | “不可思议”是计数单位
美育 | “不可思议”是计数单位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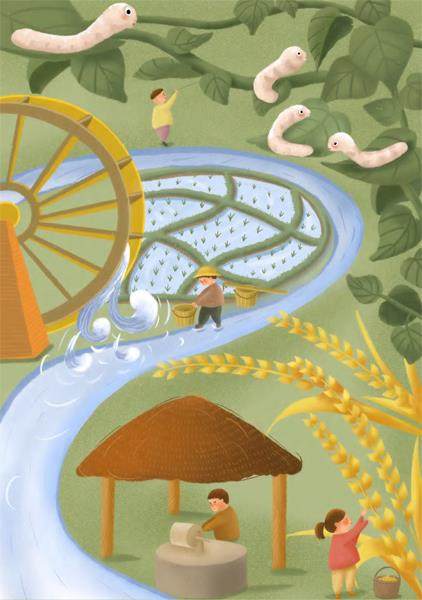
美育 | 蚕
美育 | 蚕
-
美育 | 为什么浪花是白色的?
美育 | 为什么浪花是白色的?
-

美育 | 如何让自己成为世界第一
美育 | 如何让自己成为世界第一
-
美育 | 模糊是一种美
美育 | 模糊是一种美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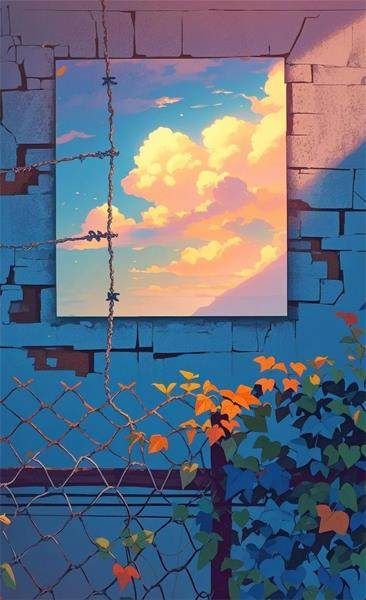
美育 | 重见
美育 | 重见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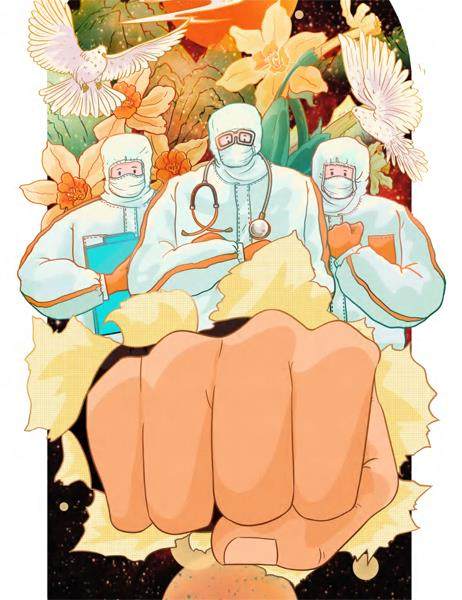
生涯 | 我做ICU医生二十多年
生涯 | 我做ICU医生二十多年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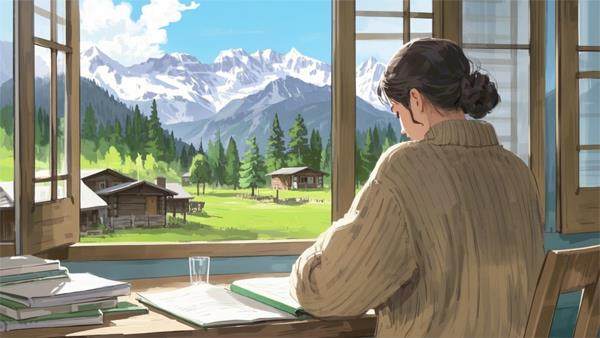
生涯 | 脱产考公的五年
生涯 | 脱产考公的五年
-

生涯 | 德云社的录取标准
生涯 | 德云社的录取标准
-

通识 | 克隆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吗?
通识 | 克隆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吗?
-

通识 | 凡事发生,皆有利于我
通识 | 凡事发生,皆有利于我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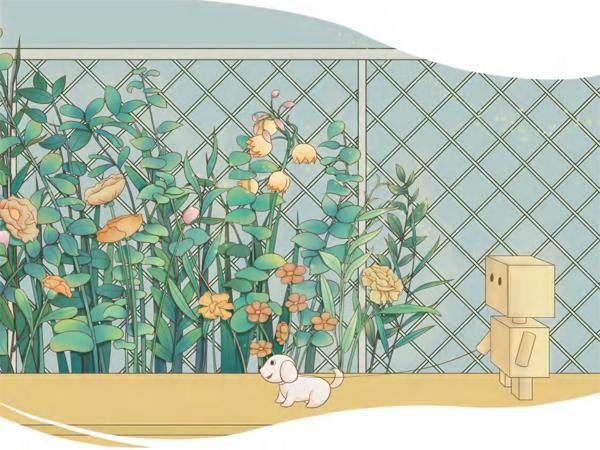
通识 | 旅行为什么不能安慰你?
通识 | 旅行为什么不能安慰你?
-

通识 | 未来的奇迹
通识 | 未来的奇迹
-

教与学 | 数学好的孩子比语文好的更聪明?
教与学 | 数学好的孩子比语文好的更聪明?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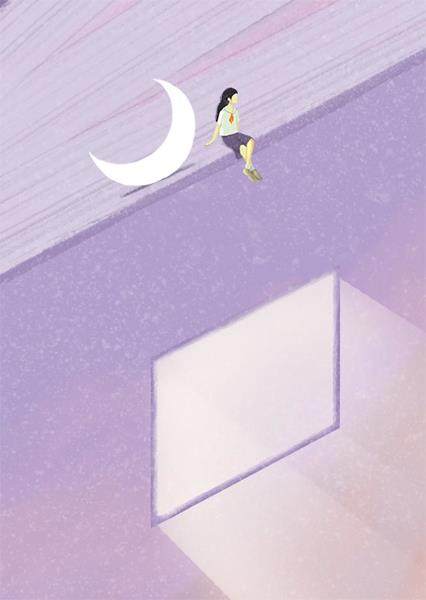
教与学 | 一所只招“问题学生”的学校
教与学 | 一所只招“问题学生”的学校
-

教与学 | 民国的学生是如何考大学的
教与学 | 民国的学生是如何考大学的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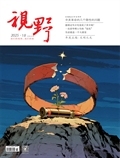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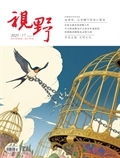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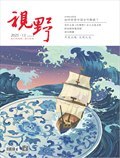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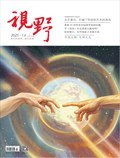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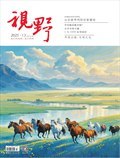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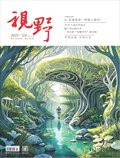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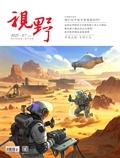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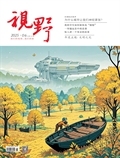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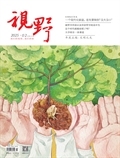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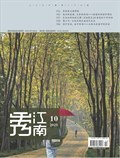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