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
开篇作品 | 风筝
开篇作品 | 风筝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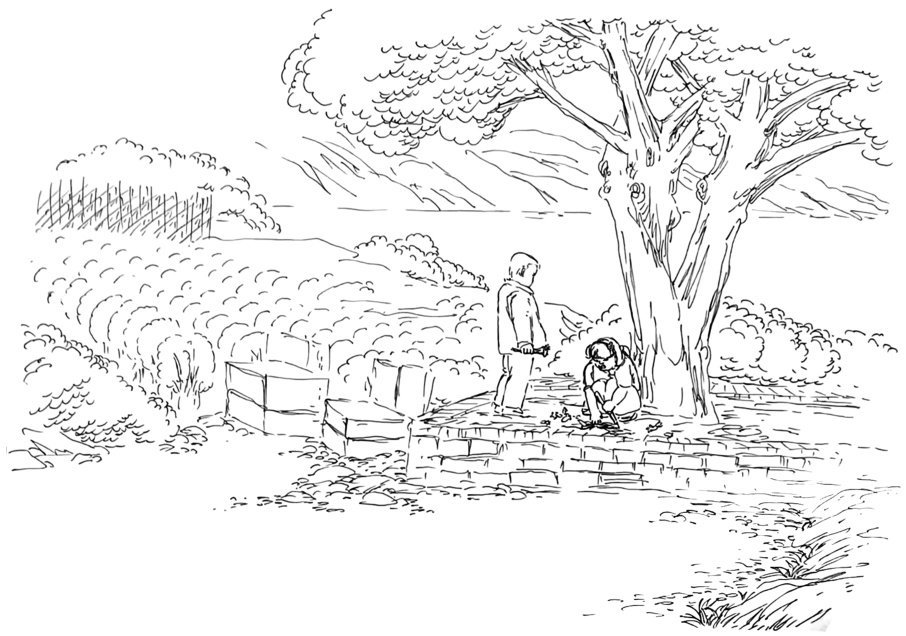
小说平台 | 榴花开尽
小说平台 | 榴花开尽
-

散文空间 | 人与畜(外一篇)
散文空间 | 人与畜(外一篇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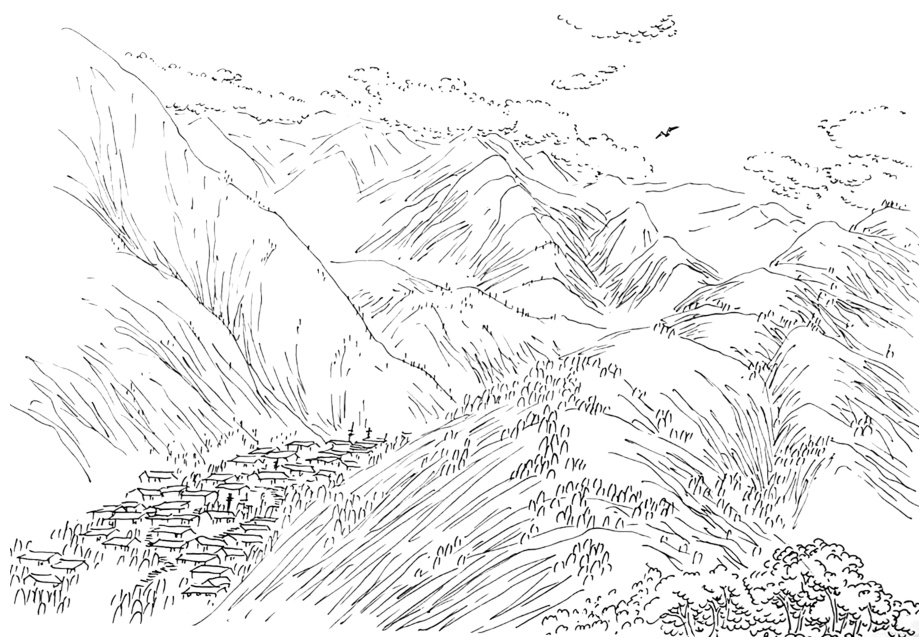
散文空间 | 脚步的踏程
散文空间 | 脚步的踏程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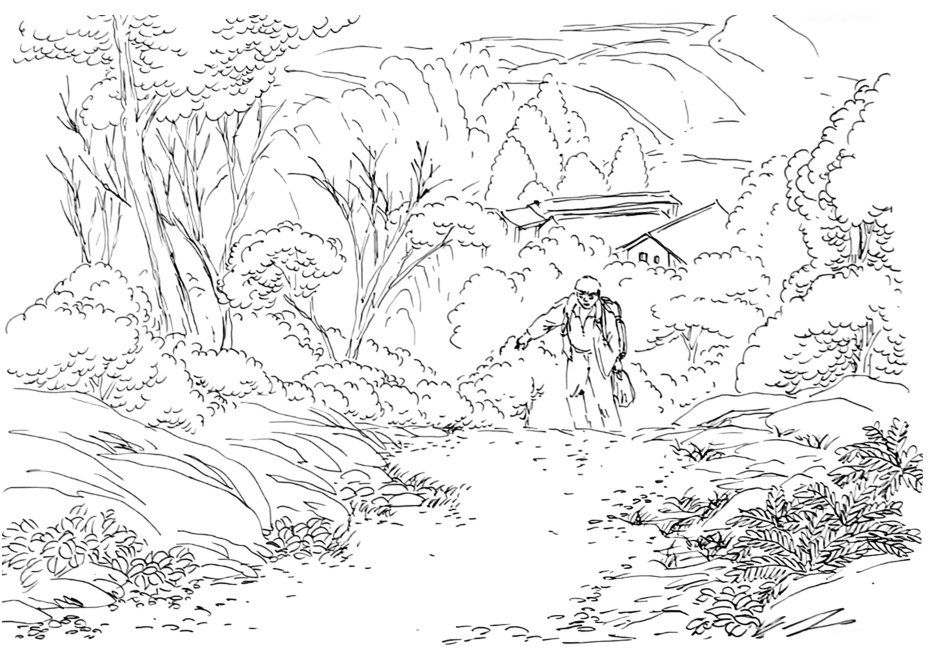
散文空间 | 一念之间
散文空间 | 一念之间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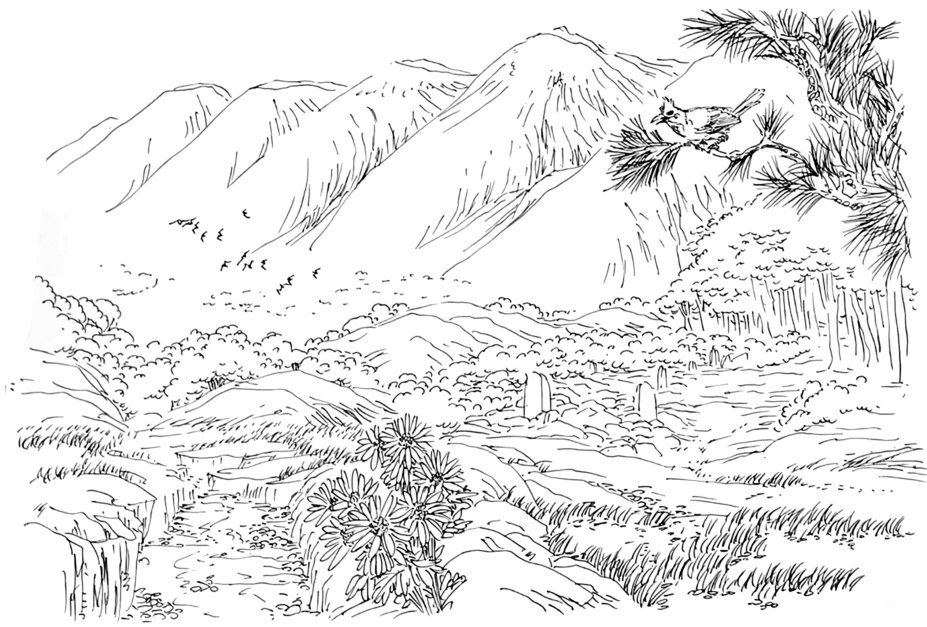
诗歌广场 | 远远乡(组诗)
诗歌广场 | 远远乡(组诗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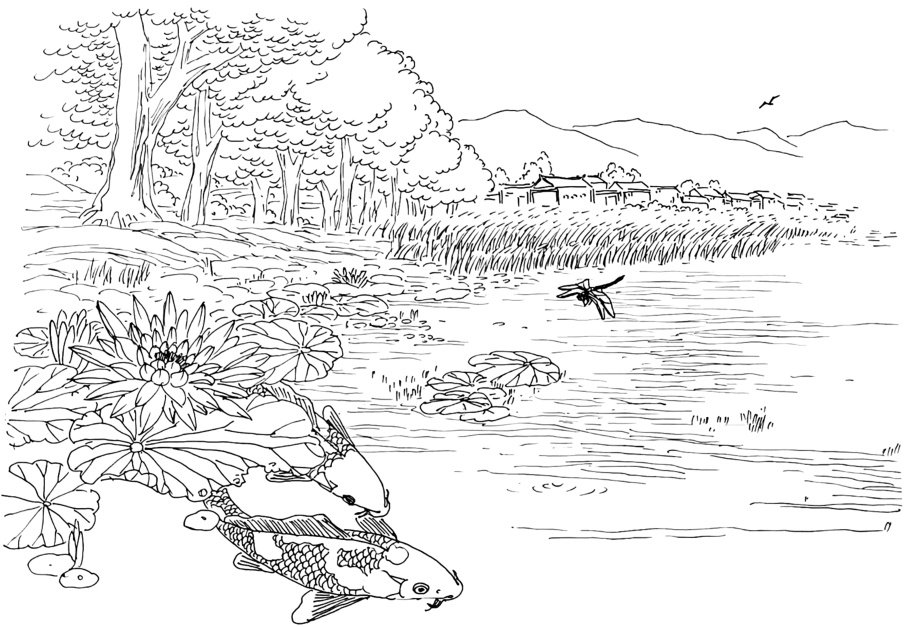
诗歌广场 | 西湖村,热烈的夏天(外四首)
诗歌广场 | 西湖村,热烈的夏天(外四首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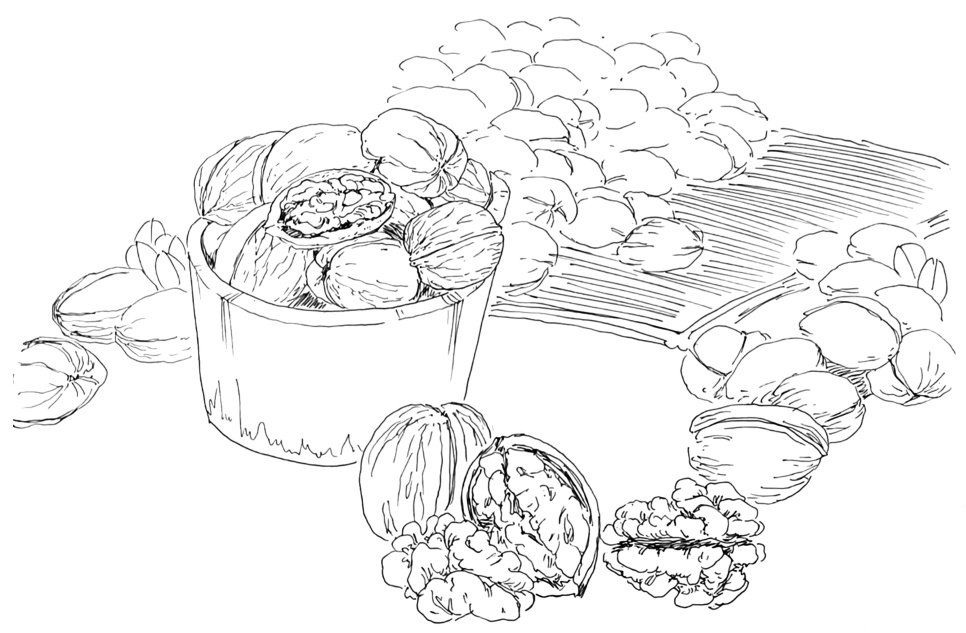
诗歌广场 | 子午镇(外八首)
诗歌广场 | 子午镇(外八首)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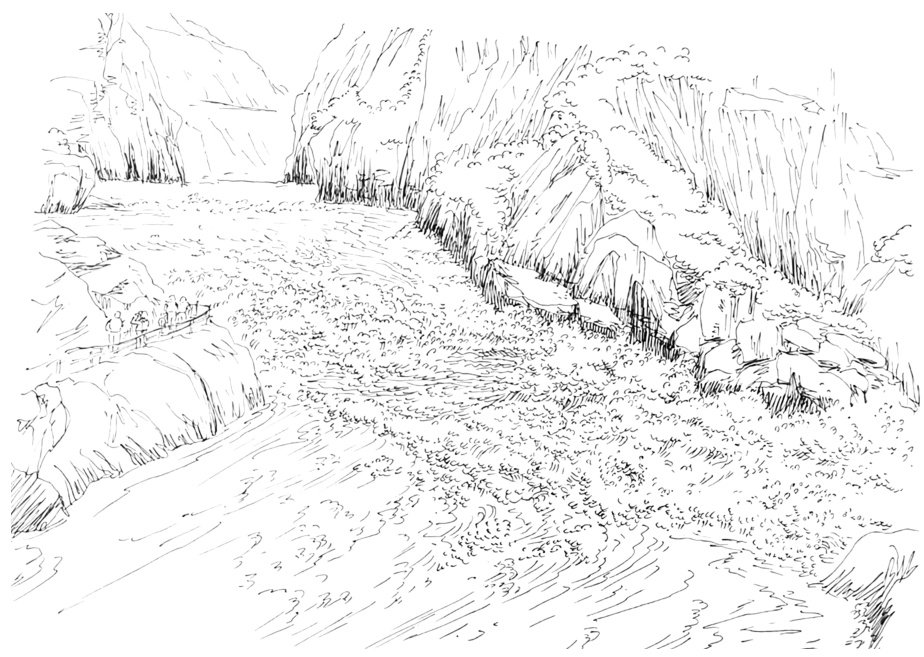
诗歌广场 | 云南行记(组诗)
诗歌广场 | 云南行记(组诗)
-

诗歌广场 | 苍洱诗萃
诗歌广场 | 苍洱诗萃
-
文艺评论 | 同一个文本,不同的聚焦
文艺评论 | 同一个文本,不同的聚焦
-
文艺评论 | 根在大理 魂在文化
文艺评论 | 根在大理 魂在文化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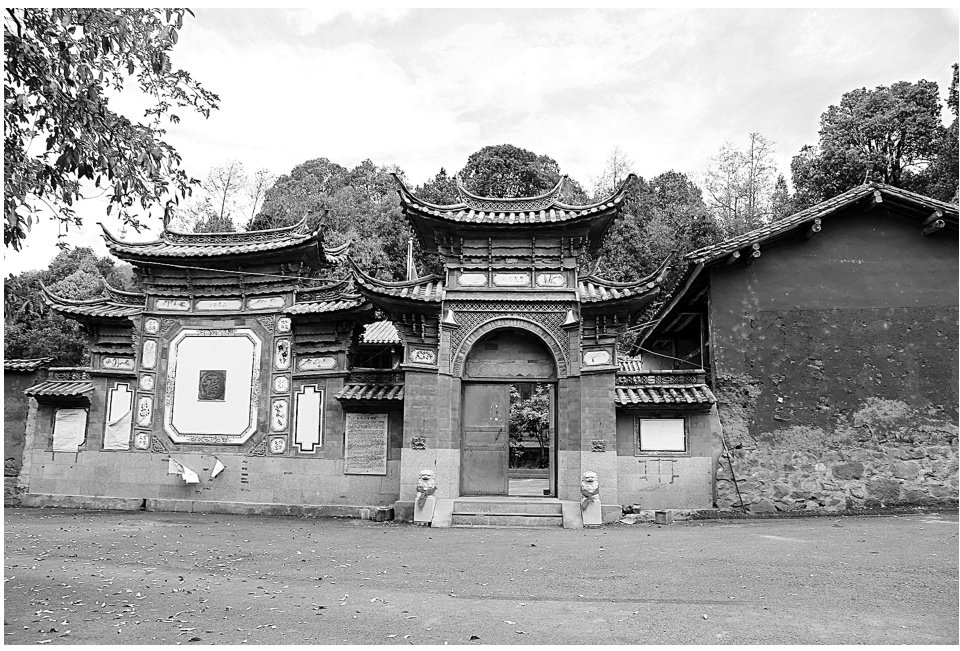
大理旅游 | 白竹山中
大理旅游 | 白竹山中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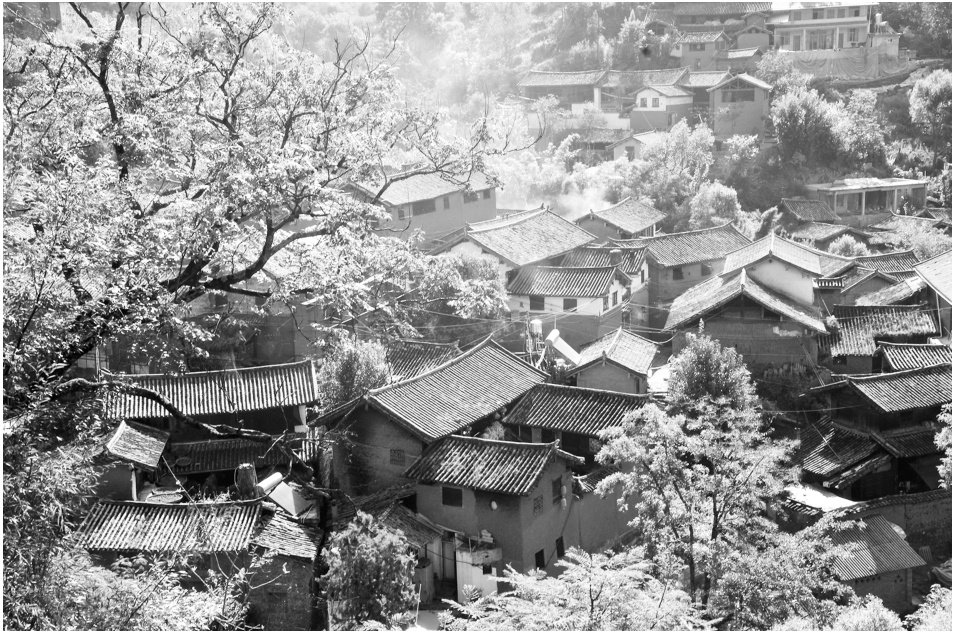
大理旅游 | 岁月深处的诺邓
大理旅游 | 岁月深处的诺邓
-

大理旅游 | 走进朵祜彝族婚礼
大理旅游 | 走进朵祜彝族婚礼
-

大理记忆 | 忆前所街
大理记忆 | 忆前所街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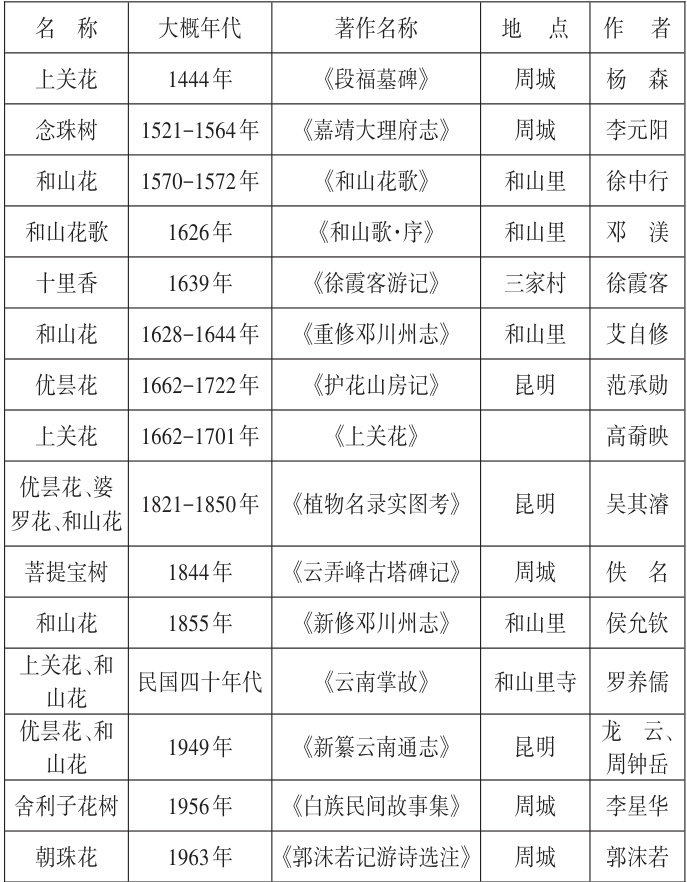
大理讲坛 | 解密“上关花”传说
大理讲坛 | 解密“上关花”传说



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