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
卷首语 | 露西在站满人类的长河
卷首语 | 露西在站满人类的长河
-

专稿 | 露西的世界
专稿 | 露西的世界
-

天文学 | 是时候拯救世界了
天文学 | 是时候拯救世界了
-

物理学 | 令人困惑的奇特的电子聚集体出现
物理学 | 令人困惑的奇特的电子聚集体出现
-
生命科学 | 演化生物学激动人心的时刻
生命科学 | 演化生物学激动人心的时刻
有人认为,自生物演化理论提出后,该领域最重大的问题始终没有改变。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,但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,人们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,以及将相关结论应用至不同领域方面的努力,都已取得巨大进展。这些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发展。更先进的技术和新的分析方法使几乎所有物种的组学数据都可生成。本文围绕领域内一些激动人心的进展展开述评。 关于生物演化,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是个体如何适应环境。回答这个复杂
-

医学与健康 | 全球第二例猪肾移植者又摘除了猪肾
医学与健康 | 全球第二例猪肾移植者又摘除了猪肾
-

医学与健康 | 猪器官移植带来的启示
医学与健康 | 猪器官移植带来的启示
-

计算科学 | 尖端计算机芯片如何加速人工智能革命
计算科学 | 尖端计算机芯片如何加速人工智能革命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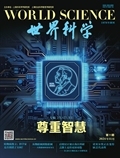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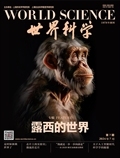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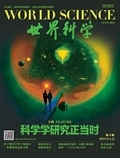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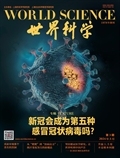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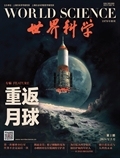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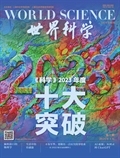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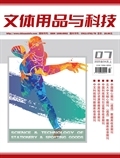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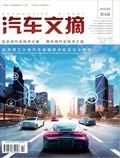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