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小说坊 | 槐花香
小说坊 | 槐花香
一 五月里槐花香 南河的水长又长 岸边的樱桃红 南湖的麦子黄 我送阿哥去战场 …… 兰槐花在睡梦中似乎又听到了那首歌谣,是她朝思暮想的天亮哥唱给她听的。声音还是那样清脆嘹亮,像是被柱子山上的山泉水洗过一样。她还是站在那棵老槐树下,天亮哥的脸庞越来越清晰:四方脸、高鼻梁、大眼睛,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……她笑吟吟地刚一招手,那可爱的脸庞忽地就消失了。兰槐花从梦里
-
小说坊 | 婚姻
小说坊 | 婚姻
1 杨光林从老家回来,疲惫不堪。四层的步梯他走了十多分钟。打开门,他把包往沙发上一扔,径直走进卧室,脱鞋,倒在床上沉沉睡去。 醒来,家里一片漆黑,他打开灯,手机显示,晚上十点三十七分。他起身走到客厅扯了几张纸巾擦了擦汗,接了一杯凉水灌下去,清醒了许多。 现在,他感觉肚子有点儿饿了。走进厨房,一周以前吃面的碗还没洗,电磁炉上蒸锅里的面汤散发出霉味,他想到小区门口的小黄牛肉馆对付一下。
-
小说坊 | 舅舅的官司
小说坊 | 舅舅的官司
自从我考入西南大学,我还是第一次回家。给爹娘买了礼物,我坐在车厢里心安定不下来,很是激动。 火车到站后,我又坐了两个小时客车才到了我家镇上的客运站。客车刚停下,我就看见爹站在站牌下等着我,脸冻得通红通红的。 我赶紧下车,跑过去,说:“爹,不是不让你来接吗?我又不是不认识家。” 爹夺过我手里的行李说:“别多说,家去吧。” 我问:“娘好吧?” 爹答:“自个儿没啥事儿。”
-
小说坊 | 儿殇
小说坊 | 儿殇
梦中,她一直追着一张照片在跑。拼命地跑,拼命地跑,她终于停在那个废弃的砖厂中央的土台子旁。 醒来,晓晓找出了那张二十五年前的彩色照片,照片上有三个小女孩。 中间半蹲着的是三岁的晓晓,干瘦的她穿着一件鹅黄的毛衣和一条皱巴巴的深色牛仔裤,像一个假小子。 晓晓的左边坐着五岁的杜馨,乌黑的齐耳短发,一双迷人的丹凤眼,讨人喜欢,唯一可惜的是她的嘴长得有点儿歪,不笑时还好,笑起来整张脸透着一丝邪魅。
-
小说坊 | 闺蜜
小说坊 | 闺蜜
一 闺蜜叫王曼,一九六一年出生,比我大两岁。我们十一二岁时就认识了,我们两家住得很近。少女时代,我们几乎形影不离,无话不说。 我叫朱丹,父母都是呼兰县评剧团的演员。我有两个姐姐,一个弟弟,一个妹妹。 二姐朱青曾警告我说:“离王曼远点儿,那个人不地道。” 二姐从小就欺负我,我好不容易有个好朋友,凭什么叫我离开她? 我三岁的时候还尿炕,没少受妈妈的数落。二姐给我起了个外号“尿
-
散文苑 | 辽西的辽塔
散文苑 | 辽西的辽塔
在中国的城乡,塔是最常见的物事。印象里似乎每条河、每条江、每座城市的高处都有塔相伴。于是,塔景、塔影、塔魂,也就成为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哪一个国人会不知道几座名塔呢?比如说河南少林寺的嵩岳塔;西安的大雁塔、小雁塔;苏州的虎丘塔;杭州的雷峰塔,不一而足。 佛塔在梵语里叫窣堵坡,是坟冢的意思,曾被音译为“浮屠”或“浮图”,直到隋唐时,才以“塔”作为统一的译名。据佛教经典,塔是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
-
散文苑 | 黄昏时分
散文苑 | 黄昏时分
黄昏时分,一阵阵浓郁、诱人的烤肉香味扑鼻而来。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大快朵颐,端着扎啤杯开怀畅饮。 每逢此时,我也在家楼下的几处烧烤摊位前无忧无虑地溜达,偶尔忍不住花十多块钱去买几根肉串,尽情地享受舌尖上的快乐。 这样的黄昏,无论是燥热难耐的夏季,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季;无论是细雨霏霏,还是晴空万里,都让我获得一种难以名状的舒适。 当女儿背着书包见到我,露出甜美的笑靥;当我张开双臂拥抱
-
散文苑 | 故乡的眼睛
散文苑 | 故乡的眼睛
入冬前,我在前洲街上碰到读高中时的季同学,无意中聊起他老家的东林庵。兴之所至,我们一并驱车前往。 一路上,季同学兴高采烈。我们开车经过塘村、田里徐家、后水门到达黄石街西街的华家宗祠,当地称作华祠堂。华祠堂于康熙年间建成,三进两侧厢,还有三间“发财堂”。院内以回廊相连,据说这里原有两棵三百多年的龙爪槐,后来不知何故消失了。华祠堂曾被改建为黄石街小学,近年才得以恢复。 没有黄石街,就没有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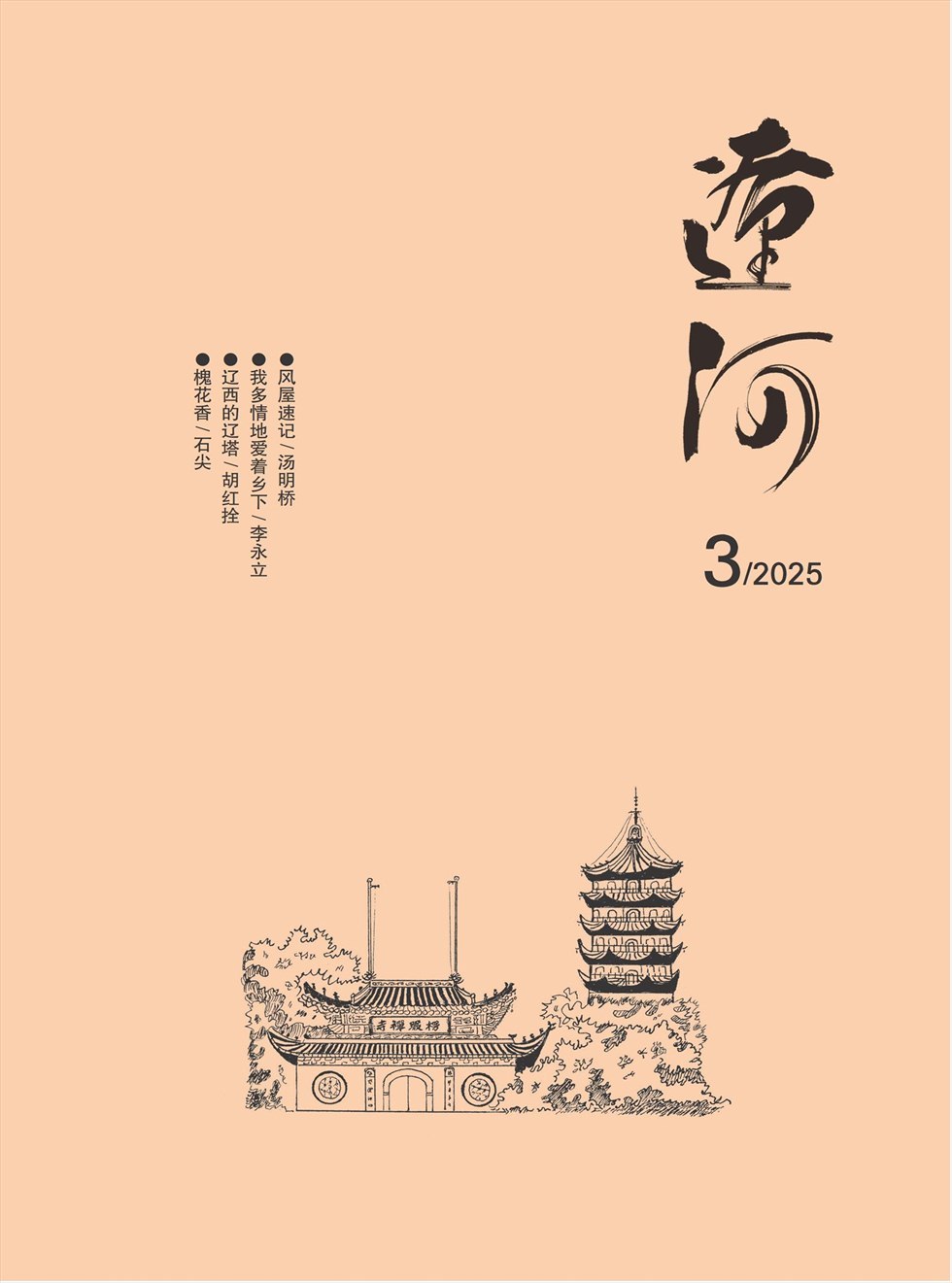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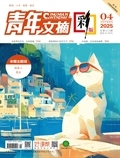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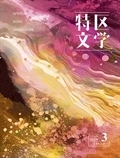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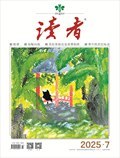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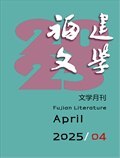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