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小说前沿 | 绿水青山
小说前沿 | 绿水青山
-
小说前沿 | 那一年
小说前沿 | 那一年
-
小说前沿 | 神鞭
小说前沿 | 神鞭
-
小说前沿 | 碎米饭(外一篇)
小说前沿 | 碎米饭(外一篇)
-
煤矿作家群 | 出发
煤矿作家群 | 出发
-
煤矿作家群 | 山冈上的火车
煤矿作家群 | 山冈上的火车
-
煤矿作家群 | 温暖的矿山
煤矿作家群 | 温暖的矿山
-
煤矿作家群 | 回声(组诗)
煤矿作家群 | 回声(组诗)
-
煤矿作家群 | 地下春天(组诗)
煤矿作家群 | 地下春天(组诗)
-
煤矿作家群 |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
煤矿作家群 |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
-
煤矿作家群 | 地火
煤矿作家群 | 地火
-
美文天地 | 芭茅林
美文天地 | 芭茅林
-
美文天地 | 牛蹄窝里的月亮
美文天地 | 牛蹄窝里的月亮
-
美文天地 | 终南草堂
美文天地 | 终南草堂
-
美文天地 | 黑天豆
美文天地 | 黑天豆
-
诗意阳光 | 被叫醒的骨气(组诗)
诗意阳光 | 被叫醒的骨气(组诗)
-
诗意阳光 | 不被自己缠住(创作谈)
诗意阳光 | 不被自己缠住(创作谈)
-
诗意阳光 | 火焰煮马的场面(外一首)
诗意阳光 | 火焰煮马的场面(外一首)
-
诗意阳光 | 夕阳斜靠在戈壁(组诗)
诗意阳光 | 夕阳斜靠在戈壁(组诗)
-
诗意阳光 | 起航(组诗)
诗意阳光 | 起航(组诗)
-
诗意阳光 | 染色的秋词(组诗)
诗意阳光 | 染色的秋词(组诗)
-
诗意阳光 | 记忆书(组诗)
诗意阳光 | 记忆书(组诗)
-
诗意阳光 | 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(组诗)
诗意阳光 | 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(组诗)
-
艺苑漫步 | 百川千河总一源
艺苑漫步 | 百川千河总一源
-
艺苑漫步 | 读许文林书法有感
艺苑漫步 | 读许文林书法有感
-
艺苑漫步 | 依心而行
艺苑漫步 | 依心而行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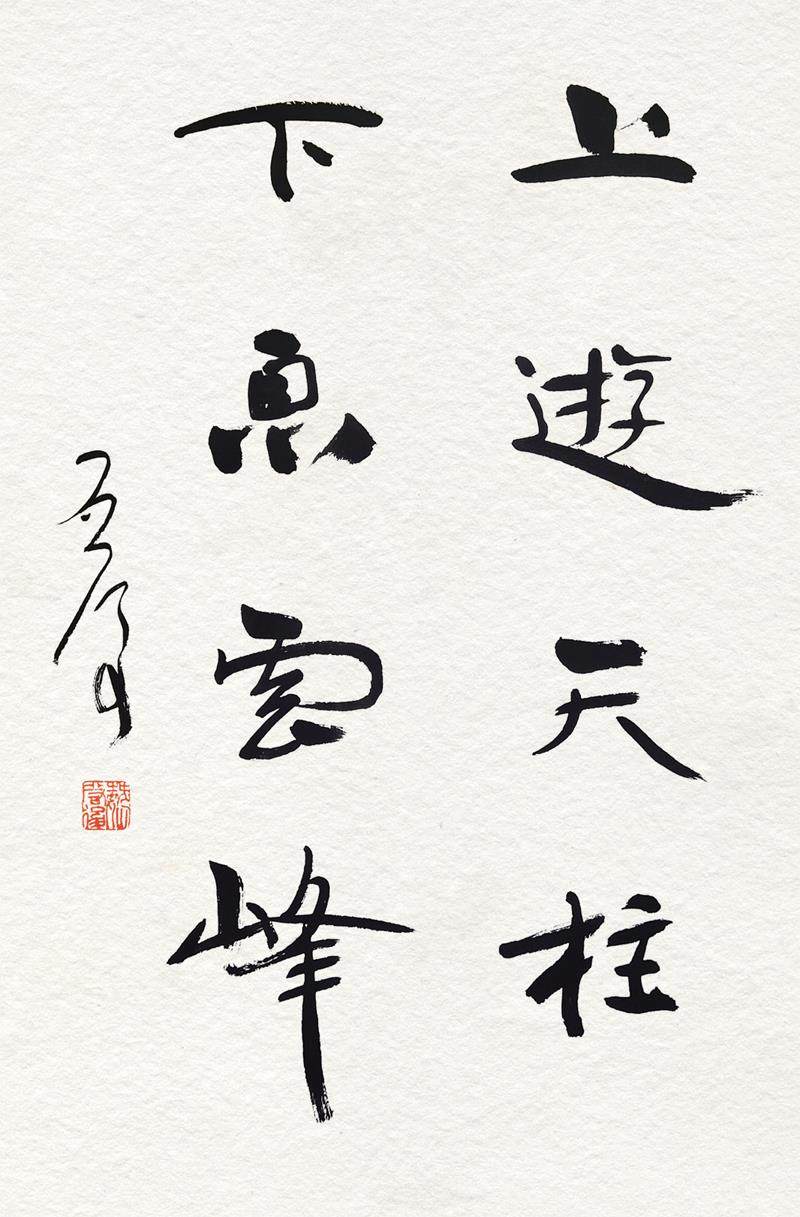
艺苑漫步 | 当代著名书画家作品欣赏
艺苑漫步 | 当代著名书画家作品欣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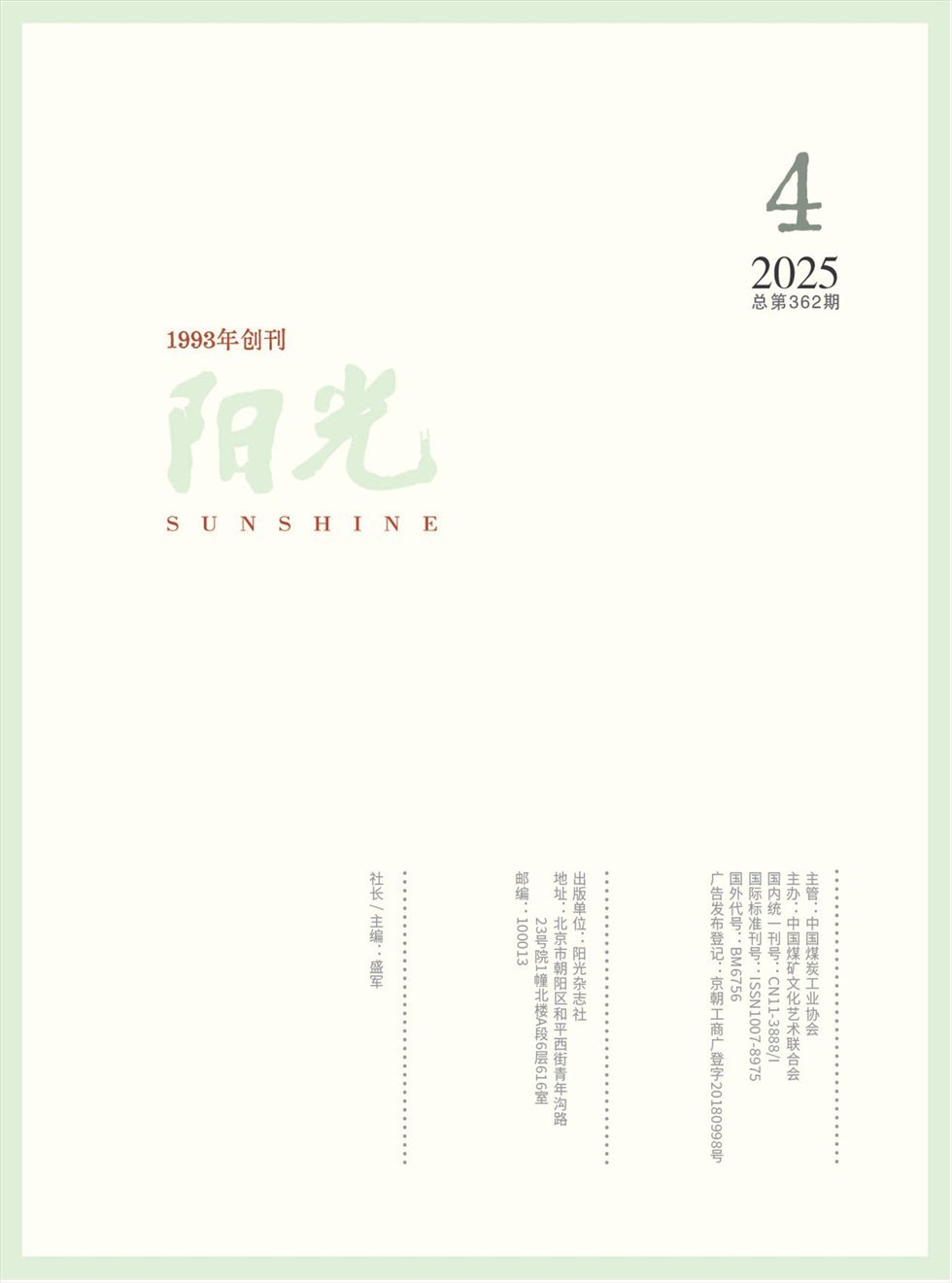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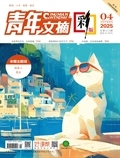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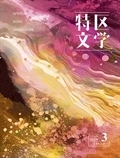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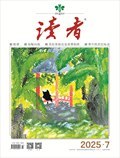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