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全部分类/
- 文学文摘/
- 书屋
 扫码免费借阅
扫码免费借阅
目录
快速导航-
书屋絮语 | 2025年第10期书屋絮语
书屋絮语 | 2025年第10期书屋絮语
-
书屋讲坛 | 读书与研究
书屋讲坛 | 读书与研究
-
书屋讲坛 | 我所认识的劳悦强先生
书屋讲坛 | 我所认识的劳悦强先生
-
学界新论 | 沅湘各自雄
学界新论 | 沅湘各自雄
-
红色记忆 | 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
红色记忆 | 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
-
人物春秋 | 茅盾佚信手稿中的一场空难
人物春秋 | 茅盾佚信手稿中的一场空难
-
人物春秋 | 金景芳与金毓黻的金石之交
人物春秋 | 金景芳与金毓黻的金石之交
-
人物春秋 | 钱基博与蔡观明的友谊
人物春秋 | 钱基博与蔡观明的友谊
-
人物春秋 | 湖湘译人俊彦多
人物春秋 | 湖湘译人俊彦多
-
灯下随笔 | 追忆林毓生教授
灯下随笔 | 追忆林毓生教授
-
灯下随笔 | 诗人·诗情·诗心
灯下随笔 | 诗人·诗情·诗心
-
书屋品茗 | 谭嗣同的桑梓情
书屋品茗 | 谭嗣同的桑梓情
-
书屋品茗 | 夏丏尊与“爱”的教育
书屋品茗 | 夏丏尊与“爱”的教育
-
书屋品茗 | 重读《金蔷薇》想到的
书屋品茗 | 重读《金蔷薇》想到的
-
书屋品茗 | 幻想尽头的生命延伸
书屋品茗 | 幻想尽头的生命延伸
-
书屋品茗 | 潮汕家谱与人物塑造
书屋品茗 | 潮汕家谱与人物塑造
-
书屋品茗 | 长沙窑瓷铭诗中的一枕闺怨
书屋品茗 | 长沙窑瓷铭诗中的一枕闺怨
-
说长论短 | 厦大期间鲁迅与林语堂
说长论短 | 厦大期间鲁迅与林语堂
-
说长论短 | 老舍与香烟的难解情缘
说长论短 | 老舍与香烟的难解情缘
-
说长论短 | 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的初译往事
说长论短 | 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的初译往事
-
说长论短 | 四十年前听君一席话
说长论短 | 四十年前听君一席话
-
域外传真 | 独立与担当
域外传真 | 独立与担当
-
前言后语 | 诗人一生在追忆中生动而丰满
前言后语 | 诗人一生在追忆中生动而丰满
-
前言后语 | 《七子之歌:闻一多新诗集》编后记
前言后语 | 《七子之歌:闻一多新诗集》编后记
-
前言后语 | 《辨喜传:爱与勇气》译后记
前言后语 | 《辨喜传:爱与勇气》译后记
-
前言后语 | 《西游记》是东方商业“圣经”
前言后语 | 《西游记》是东方商业“圣经”
-
前言后语 | 打开《诗经》之门的一把钥匙
前言后语 | 打开《诗经》之门的一把钥匙
-
前言后语 | 序《云山来信》
前言后语 | 序《云山来信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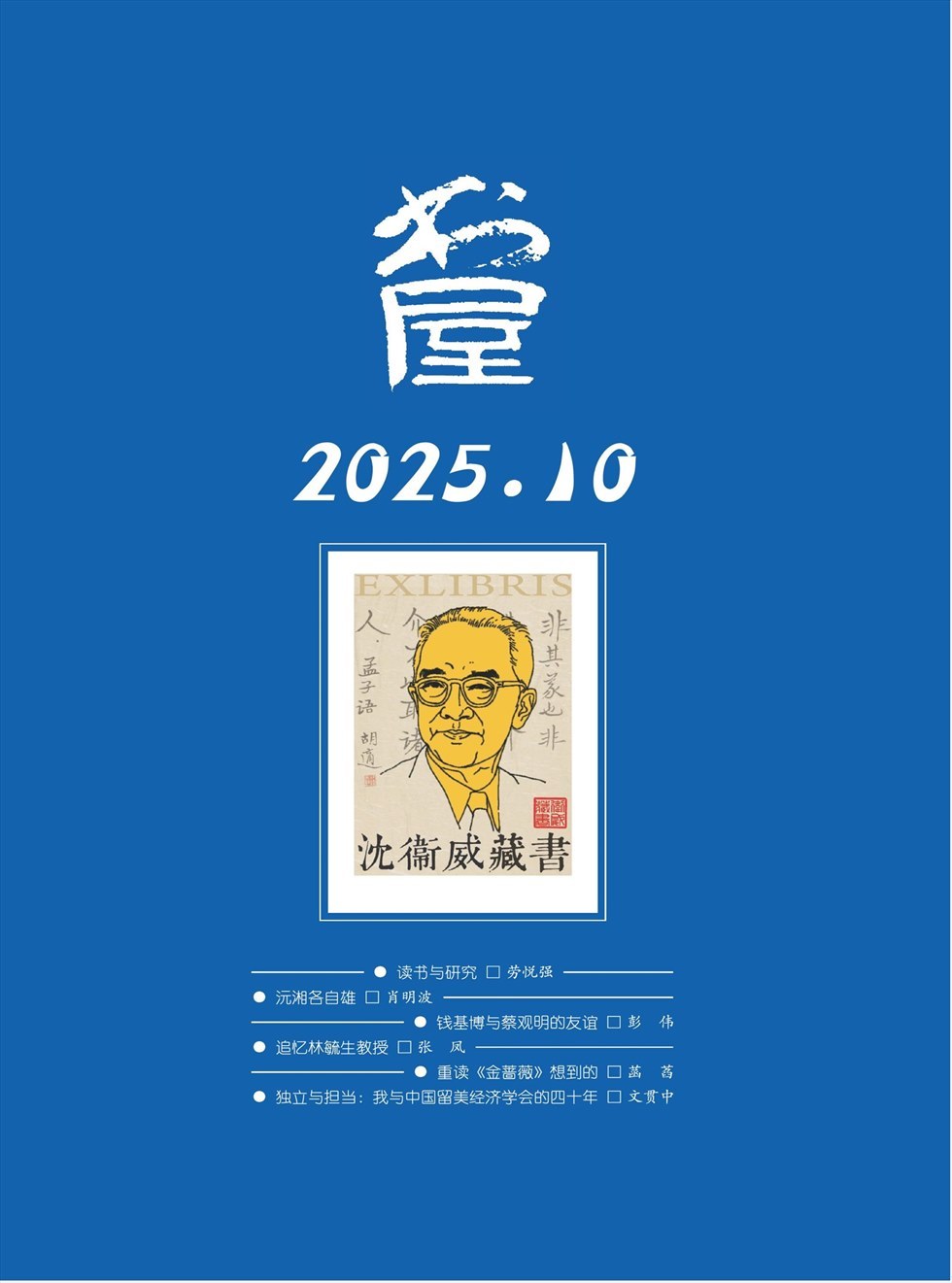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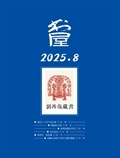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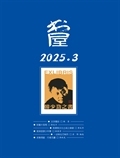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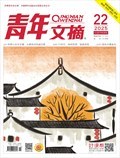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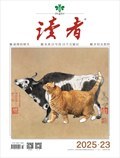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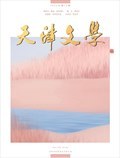



 登录
登录